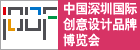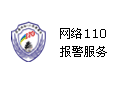陈丹青
我从初中开始学油画,跟着我的中学老师到处画毛主席像。这个时期很短,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抄家物资流到上海,使我有机会临摹欧洲的油画资料,这为我以后画“西藏组画”埋下一个伏笔。这是第一个时期,我就这么上路了。
第二个时期是插队落户期间,从1970年一直到1978年。我在江西农村,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崇拜苏联,所以我非常想学苏联画家。像我们这些知青,都没有上过学,什么也不懂,就在田里种地。如果这家伙会跳舞、拉小提琴、画几笔画,马上把他调上来,用人没有顾忌,不像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学历来看看,本科生没人要,研究生也很勉强,要到博士生越读越傻才看你一眼。所以我出道很早,1973年,我开始画连环画,居然出了三四本连环画,但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将来可以做油画家,因为油画家的门槛非常高。大家知道陈逸飞,就在我当知青的时候,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黄英浩、林旭东这些人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是那个时代出来的第一批年轻画家,也是上海解放后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年轻画家,我觉得我不太可能有一天能像他们那样变成职业油画家。1974年,我被调到省里参加油画创作,开始画革命油画,我的第一张油画创作叫做《老将和小将》。这期间我又流窜到苏北去插队。1976年左右,我得到一个机会到西藏。西藏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是我找了“文革”当中的一个特殊的题材——少数民族的题材,第二就是毛泽东去世后我可以画悲剧,可以画人在哭,因为“文革”时不可以出现悲剧场面,所有工农兵都得笑。
1980年,我忽然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在毕业创作时拿出了日后很被抬举的“西藏组画”。1978年,我考上美院之前,国内第一次邀请法国送来了一个乡村画展,这里面包括19世纪最重要的法国画家库尔贝、米勒这些人,还有一部分的印象派,这是我第一次大量看到西方的原作。当时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我觉得我可以摆脱苏联的那一套教条的画法,可以像柯罗、库尔贝那样去画画,画得小一点、朴素一点,直接画我看到的事物;第二个念头很有意思,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临摹过这些画,少年时期的记忆在那时用上了,再加上和法国的乡村画展一对头,后来就画出了“西藏组画”。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西藏组画”这么受肯定,那时候我27岁,年少气盛,就这么画出来了。
从1982年一直到1989年左右,我最痛苦的第三个时期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下子开了太大的眼界。在我出国前,我拼命想做的事情就是走现实主义道路,回到现实主义的源头,绕开俄罗斯、苏维埃的影响,回到法国的源头,同时我很真切地看到:“西藏组画”只是一个开头,我打算将来一辈子就走这样的一条路。一到纽约,我看到这些画早就过时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画挂满了博物馆,我觉得那些没有名的画家我都画不过。但这种震撼对我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很冷静地知道我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不会自我膨胀,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我个人和整个中国的油画放到当时的世界范围不足道。第二个震撼就是大开眼界,全都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又分两种,一种是从后印象派开始,立体派、野兽派、表现派、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西方最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品,也挂满了博物馆;一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画只是西方后现代艺术当中的一小块,装置艺术、地景艺术、实验艺术、观念艺术、文字艺术、影像艺术早在我停留纽约的时候即轮番上场,非常活跃。这个时候你就很迷失,你的出路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你跳进去,介入当代艺术潮流。很多比我年轻的画家就这么做了,到现在有几位朋友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蔡国强、徐冰已经赢得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普遍承认。可是我没法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实在喜欢油画,尤其是写实主义的油画,我非常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是那么多经典、那么多当代艺术,我走不下去,而且我为了卖画,为了能够生存,也没有灵感,画得不好,画得很痛苦。这个时期,我画了一张很苦恼的自画像,往塞尚那边“蹭”了一下,做了几张这样的实验。
接下来是第四个时期,我进入所谓当代的思考、当代的画面,摆脱了西藏,摆脱了19世纪美学范畴里写实主义的框架,但是我的语言没有怎么变,我的语言一直是写实的,大约最远跑到塞尚那儿,但还是写实主义。有一次我跟罗中立见面,罗中立总结我们俩的差异,他说他的画法不断在变,大家知道他画照相写实主义,然后又画乡村写实类,一直到现在画类似墨西哥壁画之类的那种,但是他的题材从来没有变过——一直在画大巴山的农民。可是我的题材一直在变化,我的画法没有太大变化。1995年,我在纽约失去了大画室,只能找一个便宜的小画室,又回到1988年时那种无聊的状态,怎么办呢?我忽然发现画册很好看,于是把画册摊在地上,开始画伦勃朗这些人的画册。在更偶然的情况下,1997年左右,我到山东出差,我对朋友说我不会画风景,也好久没画人像了,你们有没有书给我?结果他们拿来一本台北故宫藏的古代作品集,并说只有这一本,我就把那本书画了下来。这个过程给我什么启示呢?我发现用油画材料可以画国画,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把董其昌和一些宋画摊在地上画,一画差不多画到今天。
我的四个时期说明人要与时俱进。一个人的绘画尤其是写实的绘画,可能必须和个人的变化、周围的时代变化综合起来,命运会暗示你下一步往哪里走,在非常有限的领域里往前走。我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齐白石,齐白石经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而且他有生之年基本上是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一段,是充满灾难、充满大事件的时代,可这些在他的画里一点都看不到。这是另外一路,我也非常羡慕这一路。可是我是共和国的孩子,我受的是艺术反映生活的教育。现实主义艺术和人的艺术非常接近,它的艺术是有人才有你的画,有了你的画这个人才可看,它是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我在吃开口奶的时候画的是毛主席像、工农兵,然后又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追随苏维埃的现实主义油画,我觉得一个人少年时代接受的东西,他一辈子都很难改变,所以我只有把它做下去。
我今天在画书,可书里还是有人,包括山水画,山水画里也还是有人,因为中国的山水画不是跟着自然走的,跟着人走,跟着性格走,跟着脾气走,跟着学问走,像董其昌的画。所以我现在的绘画之前自己也没有料到。回国以后,情况有些变了,虽然也在断断续续地画些静物,但是我经历着新的困扰:我到美国去的时候经历过一次文化震撼、文化失落,从美国回来之后又一次经历文化震撼、文化失落,因为我走之前中国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中国完全是一个超速发展的国家,它的景观变了,它的人变了,然后它的价值观也变了,这个变有好有坏,有正面的有负面的。这一切都对我造成困扰,同时又好像出现很多机会,这时候我忽然开始写作,越写越多,直到今天。很难为情,我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写作的人,我一直对外强辩说我是一个业余作者,但事实上我知道我投入写作的时间远远多于绘画,为什么呢?因为我忽然发现我的书居然也有人买,这让我在经受困扰的同时接受了一个挺好的诱惑——不停地往下写,同时我在写的过程中发现我在绘画中很多无法放进去的感受可以写出来。
我现在又在一个歧路上——到底是该多一点画还是继续写作呢?因为永远有媒体让写东西,我自己闯的这个祸,只能自己承担,但这是一个歧路,我到现在还没决定这两条腿到底往哪儿走。
(本文根据陈丹青讲座录音整理,由江苏省南通市中心美术馆供稿)
相关新闻
- [人物专访]王轶昆:设计师需常怀利他之心(08-16)
- [人物专访]【关注两会】单霁翔:书画保护令人堪(03-04)
- [人物专访]魏鹏举:联盟化和专业化是文交所未来(02-13)
- [人物专访]秦大虎:中国油画要有中国的特点(07-25)
- [人物专访]威尼斯双年展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什么(07-22)